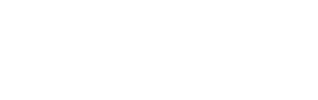博古睿讲座15 | 技术给我聪明药
技术给我聪明药,讲座实录
9月4日,在北京单向空间,由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主办、单向街公益基金会支持的讲座《技术给我聪明》暨《技术有病,我没药》分享会如期进行。约有60位观众来到线下参与了此次活动,高峰时期1.5万人在b站观看了此次直播。
本次讲座的问题意识很明确:在技术时代,我们如何自处,技术的开发者又该如何思虑和布局?享用技术的后果,还是放弃技术的便利,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恐怕都没有选择权。从手机到孟婆汤,从忘忧枣到性爱机器人,从技术拒绝到人类增强,从海德格尔到斯蒂格勒,《技术有病,我没药》这本书由杨庆峰、闫宏秀、段伟文和刘永谋四位科技哲学研究者,用8个现实问题挑起了“科技到底人类社会的毒药还是解药“之辩。
本次活动由博古睿中国中心副主任李潇娇主持,本书的两位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永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2020-2021博古睿学者段伟文——分别针对新书的部分内容做了主旨分享,并回答了现场和线上参与者的数个问题。
01 技术反叛,我们如何使其向善?
刘永谋在分享中提到,我们生活的时代,与其说是科学时代,不如说是技术时代。在古代,科学和技术是不一样的。科学是贵族的智识传统,技术是工匠的“奇技淫巧”,后者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直到19世纪下半叶,“科”“技”的一体化才真正发生,与之相关的背景是双方都需要彼此来增强解释力和影响现实的能力。
之后,技术的地位在不断提高,甚至出现了逆转“科学”占主要位置的趋势。技术在社会进程中的实际功用令其成功反抗了科学的沙文主义,颠倒了科技的主次关系,让“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诞生:一种“被压迫的知识的造反运动”正式完成了。我们正式进入了技术新世界,然后呢?
技术的合理性成为了合理性基础,技术影响的深度达致全新阈值,开始深入到人的肉身与精神。深度科技化把人悬置于过劳,悬置于无意识地被动,乃至于开始参与人类的“身心设计”。我们至多只能像从树上爬下来“不愿继续做猿猴”的露西,与技术至上的价值观告别,但不知道如何与技术共处、用适切的方式利用技术。
刘永谋指出,技术能不能被控制?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该从技术中寻找,而在于人类的选择:第一,我们有没有决心和勇气控制技术的发展,第二,更重要的是,为控制技术,我们愿意做出何种付出甚至牺牲。在一个技治社会里,向罪(沉沦)是轻松的,向善是难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药,没有人能代替我们开药、服药。
02 深度科技化时代的精神分裂症
段伟文认为,我们所处的深度科技化时代正在将世界变为基于符合的可操作系统,服从与温顺将是被鼓励的价值,技术将能参与世界的多数决策并对最终后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在这种世界里,人与自然都面临着被技术“液化”的风险——数据将把个人异化为流动的信息式的实存,人的一切行为、偏好都将普适计算;自然会成为全球交易系统中漂浮的商品,碳核算与碳交易已经在把生态环境及其属分变为可计算与可买卖的,完全不顾及环境的区域性与不可简单加总的性质(为了在一处加大排放力度从而在另一处不断种树,只会引向崩坏)。此外,世界也同样面临着被“气话”的风险:虚拟现实技术、元宇宙走向纵深,我们赖以生存的真实世界全在一个计算的世界里被消解,只留下感官上的刺激与数字的魅影。
具体地看技术时代的人,我们在进击的同时面临被驯化的危险。我们在斯普塔尼克时刻(注:苏联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1号,开启了冷战时代的太空竞赛)、广岛时刻、多莉羊时刻踌躇,在利用技术自我升级与深刻地改造地球的同时被食品安全、生态危机、技术成瘾的阴影笼罩,在自动化的浪潮里逐渐失去基本技能,被技术放逐成无所依的流民。
而当平台、资本部分垄断了技术,一些更具伤害性的事情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快发生。监控资本主义会用数据的单向镜将人降维,追逐你的每一笔消费、每一次行踪乃至每一个微表情,以此来实现商业诱惑的精准递送或一个恶托邦的全景、实时监测,隐私、界限或将消失。“数据”,将会是每个人新的“皮肤”,任何不合规、不被允许的言行都将被数据记录,成为我们数据皮肤上永远抹不去的疤痕。
面对这样一种可能的技术未来,我们需要增进思辨,不是词语游戏意义上的,而是真实地去思考,某些技术真的是我们要的吗?我们在什么时候持有说不、喊停的权利?
03 科技哲学的学科地位、技术时代的学术诚信和伦理教育
在分享结束后,刘永谋与段伟文回答了现场与线上观众的数个问题。这些问题有的直至科技哲学的时代价值与影响力,有的则结合时事热点、期待探索科技哲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一个普遍的质疑是,哲学的黄金年代早已过去了,面对强盛的资本、权力与狂热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和“工业党”,科技哲学的学科现实指向是什么?科技哲学家们是否应该,以及如何介入社会讨论,才能发挥一定作用?
刘永谋认为,技术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旋律,理解技术是理解这个时代精神的必要条件,而哲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厘清概念、澄清逻辑、设置议程,在一种普遍对技术的乐观与无感之外提出异议,在未来尚不明晰的时候帮助社会梳理出应对可能挑战的策略。哲学并不是救命药,它与其他学科一样行驶在自己的航道,不比谁高贵也不比谁弱势,我们需要哲学在乌托邦与恶托邦、理想国与机器国之间摸索,为人类找答案。
段伟文介绍到自己广泛参与产学研各界的科技哲学讨论。他认为,在一个信息爆炸、知识极度丰富的时代,哲学能起到的关键作用可能不再是形而上学层次上的,而是链接,把各行各业生产出的知识整合、梳理,分析、批判,在感受和想象上构造完整的逻辑与故事,让可能的未来场景可感、可考。科技哲学的当代价值是帮助当下的人类畅想未来,在一切还未被定夺的时候参与塑造一种可能的、更良善的技术未来,并通过普及、宣教的方式让更多人有意识、有反思。
另有提问者结合时事问到,技术时代的学术诚信如何保证?技术的进步如何影响了学术标准、以及学术不端的界定?
两位主讲人都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正深刻影响着学术产出的质量。当我们把一切学术水平归结于核心期刊文章发表的数量、影响力指数时,这种“学术”的衡量就已经失焦了。实验中的可复制性是真理性问题,不容置喙;造假是学术道德败坏,其来源可能是工程师、科学工作者的学术伦理、诚信教育不足所导致的。段伟文特别提到,我们应该对查重软件保持警惕,因为抄袭、造假的核心不是语句的搬弄——那当然是最基础的要求——而是观点的重复。查重软件的技术,对于多次来回翻译后的结果可能无能为力,但我们真正应该警惕的就是把别人的想法据为己有的行为。
此外,对于“从历史的技术治理经验中,我们如何吸取教训”这个问题,刘永谋认为在18、19世纪,科学至上的观念就已有流行,与之相对应的,也有激进的技术使用(例如切除罪犯的脑页等)。但过去与现在的差别在于,过去的技术治理应对的是化学、物理、心理的学科知识,而现在则是智能科技。数据、参数带来了智能治理的综合,也加大了进行管控与限制的难度,我们需要创新思路、提供重视。
对于“技术院校是否应当有哲学人文学者坐镇“的问题,段伟文提到了他在南方科技大学所开设的学术规范、科研诚信与技术伦理课程。他认为,针对技术背景学者的伦理教育将是未来的一个重点方向,只有掌控技术的人对技术生发出反思与审慎的态度,社会才能更好地对技术形成共同想象,促进深度科技化的未来有哲学的荧光棒为之挥舞。
04 回应书名
《技术有病,我没药》,这个书名饱受“标题党”的诟病,但两位学者似乎并不避讳。如今注意力稀缺,信息泛滥,“标题党”非常有效。读者被吸引过来,然后才可能从书中有所得。
这也是两位学者的治学风格——走出学术象牙塔,在走向社会的过程里有理、有据、有节地用哲学之思给技术时代降温。技术既是毒药,也是解药,亦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是药,没有人能代替你来开药、服药。
李治霖,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实习生] | 采写
简介
活动主办方:
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
机构
单向空间
场馆
活动时间:
2021-09-04
活动地点:
单向空间 / 哔哩哔哩直播
活动状态:
已结束
嘉宾
视频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