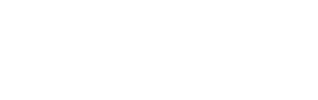博古睿讲座31|生命伦理学的双重视角:西方原则主义与儒家礼仪传统
文化传统、日常礼仪如何影响医疗决策?——生命伦理学的双重视角
2024年10月21日晚,博古睿讲座系列第31期“生命伦理学的双重视角:西方原则主义与儒家礼仪传统”在北京万圣书园举办。本次讲座由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学系哲学讲座教授范瑞平主讲,两位对谈嘉宾分别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丛亚丽、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珏。
本次讲座从“知情同意”等医疗案例出发,对比了东西方在生命伦理问题上不同的礼仪与文化传统——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我决定”的原则主义和儒家“家庭共同决定”的模式差异——探讨了在未来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如何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平衡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更好地指导生命伦理学的实践;进而追求一种既与文化相联系、又能跨越文化壁垒的适宜的生命伦理学。
医疗决策的东西差异:从原则主义到构成性礼仪
范瑞平教授首先以一则跨文化环境中的医疗争端为例,阐释西方“自我决定”与儒家“家庭共同决定”模式的冲突,这种冲突尤其体现在对“医疗讲真话”和“知情同意”问题的不同理解上。案例中,一对年迈的北京夫妇在美国就医时,女儿请求医生不要直接告知母亲的肺癌病情,而是与她直接沟通,制定最佳治疗方案。她计划根据病情发展的情况,在适当的时机以更温和的方式告诉母亲,这在中国是常见操作。然而医生却面临两难困境,因为在美国,病人的知情同意不仅是伦理要求更是法律规定。最后,医学伦理委员会决定利用代理同意书来化解冲突。在美国,病人可以签署代理同意书,指定其失去决策能力时由谁代为决策。医生通过向病人解释这一制度,征求病人的意见,是否愿意让女儿作为代理决策人,最终得到病人肯定。
以西方原则主义框架来看,中国家庭与美国医生的相异态度,是不同原则之间的内部对立。比彻姆与邱卓思(Beauchamp T L, Childress J F.)在《生命医学伦理原则》(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中提出的原则主义,是西方乃至全球范围内主流的生命伦理学理论——尊重自主原则(respect for autonomy)、不伤害原则(non-maleficence)、有利原则(beneficence)及公正原则(justice)——这四项基本原则构成了指导生命医学伦理实践的道德核心。女儿隐瞒的动机是为减轻母亲的心理负担,避免给治疗造成阻碍,她的初衷是为了母亲好。表面上,这是有利原则和尊重自主原则的对立,实则是现代西方尊重个人自主原则和儒家文化传统中“尊重家庭自主原则”(或“尊重关系原则”)之间的冲突。西方强调个体在医疗决策中的主导地位,而儒家文化传统则注重家庭自主原则。
在范瑞平教授看来,这种冲突其实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礼仪的构成性原则(constitutive principles)之间的冲突。构成性原则不同于调节性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s),后者追求抽象的普适性(如上述的四原则),而礼仪则以构成性原则为特点,强调人们在具体情景下如何说话行事,从而构成合适的行为或美德,反映了细节性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是有血有肉的道德生活规范。
一方面,礼仪的构成性原则限定和细化了调节性原则。例如,在中国大陆,敬酒和相互招呼共饮被视为尊重客人的表现;而在中国香港地区,尊重客人则是让客人自在饮酒,很少敬酒。两种礼仪方式都遵循“对客人友好尊重”的调节性原则, 但由于构成性原则不同,表现形式截然不同。
同时,构成性原则有助于解决不同调节性原则之间的冲突。比如在朋友请客吃饭时,面对朋友特地点好的招牌菜,即使自己不喜欢,也会礼貌地表示感谢和认可。这种礼仪让我们在面临诚实原则和友好原则的冲突之际,作出恰当的社交选择。
王珏教授认为范瑞平教授对于调节性原则与构成性原则的区分非常重要。她借用西方汉学家的观点,以握手礼为例,指出礼仪并非只是繁文缛节,而是支撑人类社会活动的核心。在此过程中,人与人相互接纳并形成链接,进而形成双方共同参与的意义空间。礼仪作为构成性原则,通常以惯习的方式呈现,依靠实践与模仿而非直接告知的方式而习得。儒家传统正是从礼仪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人类的道德实践,强调根据不同条件决定行为方式,而非如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那样给出具体原则。礼仪的构成性特征也使得同一礼仪因语境和视角的差异显现出不同的样态。例如,在大学课堂上,学生认为,坐在教室后排既表达了对老师的礼貌又可以保持个人空间。但从老师的角度看,这种距离降低了课堂的互动效果,是对课堂不重视的表现。礼仪的意义和表现受到具体情形的影响,存在解读空间和调整余地。理解双方视角,纠正偏差,寻找彼此都认可的平衡点,是实现更为和谐的互动的关键。
在具体的医疗情境中,儒家礼仪追求正是和谐的医疗决策。在范瑞平教授看来,西方个人决策模式与儒家家庭决策模式各有优劣得失,各方都不应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或“取代主义”态度。在儒家伦理传统中,家庭成员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纽带,他们共同维护家庭的整体利益和每个家庭成员的生命价值,对彼此负有道义责任。当某位家庭成员患病时,其他成员有责任积极回应并参与到决策中。若病人、家属、医生出现意见分歧,可通过加强交流、理性商讨的方式解决,也可邀请更多亲友加入讨论,集思广益,以得到妥帖的诊疗方案。范瑞平教授认为,以家庭为基础的医疗决策模式,呈现出家庭主义生活方式的生命意义和伦理价值,非但不是“落后”的选择,反而能在有效沟通与协作下,发挥出更大优势。
范瑞平教授强调,就儒家生命伦理学而言,家庭、个人与医生,都不应该凌驾于其他任何一方之上,排斥其他人的意见。各方应友好交流,以病人的福祉为核心,做出恰当的选择。尽管西方个人主义的模式能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属负担,但也导致病人缺乏必要的关怀和扶助,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重病困境中,个人往往在身心双重压力下变得脆弱,渴望能依赖亲密关系,做出理性的、有利的决策。尤其是重症监护病房中的患者,他们其实已无力自主掌控自己的行动和命运。在这种情况之下,儒家倡导的家庭生命共同体理念,能为病人提供更坚实的支撑,有利于临终关怀服务。
三地知情同意模式:医生、患者与家属的文化角色
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范瑞平教授、丛亚丽教授与美国休斯顿的医生共同研究美国休斯顿、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三地的知情同意模式。据他们观察,医疗决策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显著的礼仪差异。在休斯顿,当面临重大医疗决策时,医生会直接和病人沟通,尊重病人的个人自主权,这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体现。家属若要参与决策,须得到病人的明确同意。在公立医院,家属的加入原则上需要病人签字许可,确保决策过程以病人为中心。在中国香港,家庭共同体得到了重视,遇到重大疾病时,医生会邀请家属一同参与讨论,无需事先征得病人同意。而在中国大陆,医疗决策往往首先与家属沟通,尤其是在涉及癌症等严重疾病时,医生通常会先告知家属,再由家属决定是否告知病人,何时以及如何告知。这种方式更多体现了对家庭关系的尊重和保护,但有时也会导致病人被隐瞒真实病情。
丛亚丽教授补充道,从2005年的研究至今,中国医疗决策中的家庭决定权依旧强势,并未发现显著变化。家庭决定向来是重大事务的首选模式,尤其是生病这种关键时期。有行为能力的患者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并非因为能力受限,而是受到家庭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以肿瘤患者为例,他们虽具备参与决策的能力,却常常被隐瞒病情。而且家庭常常为了治疗患者做出巨大牺牲,甚至为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而不惜倾家荡产,牺牲其他家庭成员的利益。家属往往认为,对家人的隐瞒和无私的牺牲,是出于保护患者和坚守家庭责任的目的。但过度保护也会给患者带来负担,他们可能对家庭的压力感到愧疚与困扰。而医生在处理病情时,考虑到职业活动的安全性,更倾向于听从家属的意见,从而避免令家属不满及后续可能涉及的医疗争端。
范瑞平教授认为,医疗决策往往涉及人性的复杂性和个体内部的认知矛盾。不少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希望了解自己真实的病情,但在面临亲人疾病时又受文化积习影响而选择隐瞒对方;同时,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分歧。这可能反映了个体在渴望自主权利与认同传统美德之间的拉锯、以及伦理学研究在所谓“正当”与“善”之间的张力和冲突。
语境的融合: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的平衡
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的决策模式各有优劣,难以简单用对错来评判。丛亚丽教授强调,生命共同体观念虽有利于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无助感,但过分仰赖家庭主义可能会违背他们渴望自主和知情的深层需要。范瑞平教授认为,人的深层需要是在生命共同体中体现和追求的。许多病人在生死关头宁愿选择不去深究,保持一种模糊的“希望”,而非冷静地求知存活率,而家属和医生则默契地维护这种“希望”。
某些情况下,完全披露会危害患者的身心健康,损害指导性干预的效果。过度依赖家庭也可能导致家属大包大揽,病人消极无为。这充分说明:单一的个人决策或家庭主义都不能满足病人和家庭的复杂需求,特别是面对临终疾患等生死决策时,强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泛道德准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样就忽视了人际关系和临床事态的复杂性。医生和家属需要对病人面对死亡的脆弱性和心理状态保持敏感。
此外,王珏教授从谱系角度揭示出:西方自主原则的提出,最初是为了抗衡医疗实践中的家长主义。由于医患双方在知识和权力上的不对等,知情同意能保护患者的利益。就针对个体的治疗来说,尊重知情权合情合理;但换个角度,医疗实践也可以被理解为医生帮助家属照顾病人的活动,因此它所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和家庭面相,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维度。
个人决策和家庭决策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真正有效的家庭决策包含个人意愿的实现,儒家礼仪传统为如何平衡两者提供启示。王珏教授指出,儒家有其独特的道德规范,即“和谐”,强调在特定情境中根据和谐的需求来决定行动。面临重大的生命伦理困境时,可以融入和谐规范,灵活调整礼仪的表现,避免生硬的道德压制。例如,在机器人养老的案例中,仅靠西方原则主义的自主性原则,难以妥善解决当代养老问题涉及的利益冲突。一方面,机器人为老年人提供便利,使他们不必依赖他人,提升了他们生活的独立性,这是自主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机器人的监控功能也可能侵犯老人的自主性,老人会因受控于子女或护理人员而感到不安。儒家礼仪提供的不是强加的规则,而是协商和调节的可能。家庭成员可以借助礼仪协商,达成大家都相对满意的安排。
文化冲突的普遍性,使得寻找语境融合的支点成为迫切需求。王珏教授通过一则美国伦理学家的行医案例,说明即使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也能摸索出一种共识。案例中,虽然家属最初强烈反对向患者披露病情,但长远看,这有助于家庭内部的沟通和团结,并为患者和家属提供充足的时间,为最后的告别做准备,最终家属理解并认可了医生的决定。
在涉及患者知情权和家庭和谐的伦理诉求的冲突中,双方仍能找到理解的空间。这种理解的空间揭示了“最小的普遍主义”的可能性,这种设想基于跨文化的共通性,旨在达成各文化普遍认同的底线伦理。范瑞平教授指出,普遍道德的定义和适用范围的界定依旧是一个难题,即便大家普遍接受“不伤害”原则,各文化的解读和执行方式也存在差异。例如,当家长与孩子讨论“在日常对话中是否允许打断对方”时,孩子坚持形式完全对等的平等,即打断对方的次数应该相等;而家长则从经验出发,主张一种“不完全平等”的规则。这凸显了一个基本问题:普遍平等原则在具体操作中可能因个体身份、年龄和情境而复杂化。
互动环节
在现场互动环节,一名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同学分享了她的研究观察,她通过访谈发现,许多乳腺癌妇产科肿瘤患者会被直接告知病情。在与一些医疗从业者的交流中,她了解到,许多医生也希望能推进个人自主模式。丛亚丽教授进一步指出,在现代信息化的背景下,由于患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检查报告,隐瞒病情只能在病情初期,并且通常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范瑞平教授认为,医疗案例的复杂性往往是全部知情或全部隐瞒,而是在于知情到何种程度或隐瞒到何种程度。
有观众询问,香港本地的医院如何处理病人和家属在治疗决策上的分歧。范瑞平教授解释道,当地的公立医院提供免费治疗,私立医院多数患者也保险,因此在治疗方案上病人和家属的意见一般较少出现分歧。在涉及终止治疗等终末期决定时,因为大部分病人不会提前立生前预嘱,决策权通常交由家属。与中国大陆不同,中国香港的公立医院资助制度是直接给予医院,因而医生在医疗资源的使用上有一定的主动权。如果家属同意终止治疗,医生即可实施;但若家属不同意,则情况就会变得复杂。如果医生认为在某些情形下最好不要过度治疗,那么医生本人则需要较高的沟通技巧,平衡家属的意愿与自己的专业判断。
有观众询问,儒家礼仪传统是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或后果主义倾向,比如对知情后对病人生活的实际影响考虑过多。丛亚丽教授赞同儒家文化中存在后果主义元素,这种后果主义体现了为他人“好”的义务导向,但也带来了为“和谐”而淡化自主权的现象。有观众质疑儒家传统中的“纲常伦理”是否带有强权色彩,例如儒家是否真的鼓励内部沟通和协商。范瑞平教授指出,在任何文化的传统礼仪中,都可能存在好与坏的礼仪,孔子也对不合理的礼仪有所批判。儒家传统并不绝对地肯定所有礼仪,其核心取向乃是敬重和关爱人,而非强权。基于“仁义礼智信”的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一定会也应该会鼓励家庭内部协商。
有观众从生命和他者的视角出发,思考医疗实践能否超越直系亲属关系,允许朋友等其他关系参与进来。范瑞平教授以养老社会学的研究为例,指出老人在进入养老院后,相较于其他亲朋关系,直系亲属的探视频率高得多。几乎在所有文化中,不同于朋友关系的流动性,家庭关系因其亲密和持续的特点,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扮演了根本的支持角色。
在关于“和谐”的探讨上,在场的嘉宾们进一步指出,在西方语境中,“harmony”可能带有负面含义,暗示了对异见的压制或强求一致。而在儒家哲学中,多样性恰恰是和谐状态的前提条件。以古代典籍中的音乐隐喻和阴阳五行为例,真正的和谐不是单一元素的主导,而是各种要素通过适当的配置以达到整体协调。儒家的和谐,倡导通过互相理解、妥协,以及创造性转化来实现共生。这种精神不仅对医疗情境适用,还能为更广泛的文化对话提供指引。
文字整理:实习生 何奇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