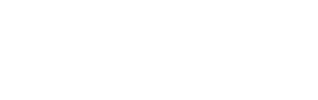世界思想家系列|“功利主义”是什么?不是什么?
10月11日晚,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与中信书店在其启皓大厦店合作举办了2024年度“世界思想家”系列讲座:“对话彼得·辛格:‘功利主义’是什么?不是什么?”著名哲学家、2021年博古睿哲学与文化奖得主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教授主讲,来自复旦大学的白彤东教授、武汉大学的刘晓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田洁副教授评议,“功利主义”实践者李治霖担任主持。
辛格教授首先介绍了“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历史缘由,并且澄清了围绕utilitarianism的几个常见误解。白彤东、刘晓飞、田洁三位教授分别就各自对utilitarianism的理解,以及该概念在中国的实际意义与辛格教授展开了对话。之后几位嘉宾与现场130多位观众进行了问答互动。
Utilitarianism与后果主义
辛格教授介绍说,“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是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伦理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后果主义的核心原则在于,通过评估行动的后果来判断其道德价值——如果一个行为的后果优于或至少不劣于其他可采取的行动,那么该行为在道德上就是正确的。
所谓“后果”,尤其是好的“后果”,可以指任何被认作有价值的事物,如快乐、美、知识、自由、公义,或这些概念的集合。有少部分“满足型后果论者”(satisficing consequentialism)认为,关注“最佳价值”时,从中获得的效益只要能达到一种能够令人满意的水平即可,因为这样能够降低对人们的道德要求。尽管如此,大多数后果论者的目标仍然是:从被认为有价值的事物中追求效益最大化。
简而言之,“功利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追求普遍适用、追求最大化福利的后果主义伦理理论。根据此理论,行动应考虑全社会的利益,而非仅关注个人。
对utilitarianism的误解
辛格教授首先提出的关于“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误解,即“功利主义”的中文翻译。辛格教授的研究助理谢业辉先生解释说,在中文语境中,尤其是日常对话中,“功利”常被解读为“(追求金钱的)利己主义”,这种带有贬义色彩的内涵容易使人误解该理论的真正含义,尤其是“功利主义”实则与利己主义完全对立。因此,他们建议至少暂时将其译为“效益主义”(遵照此提议,后文统一使用“效益主义”翻译“utilitarianism”),以强调效益最大化的伦理目标。辛格教授也期待有更适合的中文翻译出现。
其次,辛格教授从效益主义概念的发展史出发,澄清了“传统效益主义只关注幸福而忽视痛苦”的误解。效益主义,以及“传统效益主义”/“享乐效益主义”(hedonistic utilitarianism)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18世纪首次系统提出。此后,19世纪的两位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也为效益主义的学术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边沁提出的“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幸福”的口号确实容易让人产生效益主义只关注幸福而忽视痛苦的误解。实际上,效益主义强调将幸福视为内在价值,主张行动应增加快乐、减少痛苦,以实现道德上的最优结果。
边沁反对漠视其他物种的苦乐,指出动物的痛苦也应纳入道德考量。虽然幸福难以精确衡量,但效益主义者主张通过粗略比较来评估行为对幸福的影响。例如,在工业化养殖中,动物的痛苦显著高于人类享受美食的快乐,效益主义因此反对这种不平等的福利分配。
第三,效益主义关心的不只是人类的福祉。自效益主义的概念提出以来,在没有人关注非人类动物、没有国家设立动物保护法规的情况下,效益主义者就已经开始考虑非人类行动主体,尤其是动物的福利。边沁认为,若人与动物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便不应因物种而区别对待、不应因伦理只适用于人类社会而将动物排除在外。效益主义者主张,应对相似的利益给予平等的考虑(equal consideration of similar interests)。
另一个关于效益主义的误解认为:它所关注的效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经济效益等同的,例如将其理解为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化,并因此认为它与资本主义或家长式专制(paternalism)有直接联系。确实,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可以带来幸福的增加和痛苦的减少,这是效益主义提倡的目标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最大化经济价值未必是最大化民众幸福的最佳方式,经济价值与幸福、痛苦应当被分开看待。效益主义对这类问题持开放态度,它既不支持资本主义、也不偏向社会主义或家长式专制。
对utilitarianism的反驳
最后,辛格教授指出了一些针对效益主义的常见反驳,并给予了简要回应。
首先是对幸福能否量化的质疑。如先前所说,效益主义涉及“一个行动能否创造更多幸福而非不幸”的命题。辛格教授认为,很多情况下我们不需要精确量化,而是可以通过粗略比较得出判断。例如,与营养价值相似、但不需要任何动物受苦的植物性食物相比,工业化养殖中的动物被迫在不适宜的环境中度过一生,它们所承受的痛苦显然超过了任何人吃这顿饭所获得的快乐。辛格教授指出,伦理学理论不应忽视这种粗略估计。如果确实无法量化,也可以通过所谓的预期价值(expected value)进行决策,即评估各种可能后果的价值,再与其发生概率相乘。不过,现实的复杂性会增加这种计算的难度。
另一种反驳是:效益主义并不会直接导致不道德的行动,但有时会违背人们的道德直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兄弟中的一人问另一人,是否愿意通过折磨一个孩子来创造一个乌托邦世界。辛格教授认为,在这种纯粹假设的情境下,不应完全依赖直觉,因为道德直觉源于人们在当前世界的生活经验,不同环境中产生的道德直觉可能有所不同。也正因如此,效益主义的批评者在纯粹假设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并不能构成为反驳效益主义的依据。
此外,有人认为应以他人的动机和目的,而非单纯的后果来评判他人。效益主义者也同意,在评判道德主体时, 意图和动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假设有人为了获得大额奖赏救下溺水的孩子,效益主义者会认为这个行动是好的,但同时强调,不应褒扬只在对己有利时帮助他人的人。在此,辛格教授再次强调了效益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区别,同时指出,效益主义者对“行动的好坏”和“行动者是否应受褒扬”做出了区分,并认为这正是考虑动机和目的的恰当位置。
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中提出了另一种对功利主义的反驳:如果有一台机器让人获得任何想要的体验,对享乐主义者来说,理性的做法就是进入这台机器。然而,诺齐克相信,大多数人不会愿意进入这台机器,并据此得出“大多数人并不只关注体验的质量”的结论。但辛格教授认为,这一例子并不能有效反驳享乐主义或享乐效益主义,毕竟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器,也能被视为好的结果。
还有一些反驳认为,效益主义忽视公平、分配正义和权利。实际上,效益主义并非忽视这些因素,而是认为它们在本质上虽非必要,但作为手段和工具极为重要。例如,一个公平的社会通常会带来更多幸福、减少痛苦,因为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可能为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工作。类似地,效益主义支持将更多资源分配给最贫困者的原因是这种方法能最大化效益,而非因为这种行动在本质上是好的。
评议与回应
白彤东教授为当前“功利主义”的中文译法辩护,他指出,“utilitarianism”一词在英语中也常常被认为与同情心相悖。他引用了辛格著名的“溺水孩童”思想实验,强调这一实验提出的道德困境。辛格教授在文章《饥荒、富裕与道德》(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中举例:设想你在一个浅水池旁走路,看到一个孩子溺水了。尽管救助孩子可能会弄湿你的衣服,但与孩子溺亡所带来的后果相比,这一代价显得微不足道。辛格在文中认为,这一情境强调了我们在道德上对行动的义务。而正如你有责任救助淹水的孩子,你同样有责任帮助那些遭受饥荒或贫困的人,即使他们远在千里之外。
白教授认为这一观点与孟子的思想相呼应,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认为人们在面对他人危难时自然会产生怜悯之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表明,我们对他人痛苦的关注并非出于个人利益,而是源于人性中的同情。因此,辛格的思想实验不仅挑战了我们对近距离与远距离责任的理解,也揭示了普遍的人道主义义务。
针对白彤东教授的评议,辛格教授指出,“utilitarianism”在英语中并不算贬义词,追求快乐的想法也不应被视为低级。密尔尽管也区分高尚的快乐与低级的快乐,但他在此的区分另有标准。此外,辛格教授提到,亨利·西季威克的伦理学很深刻,至今仍然是理解古典效益主义的较好资源。最后,辛格教授探讨了人类保护自己孩子的本能与自然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我们应重新评估自然,并可能接受一些不自然但更好的选择。
刘晓飞教授分享了效益主义常常与普遍的道德观念相冲突的观点。例如,陈嘉映教授在《救黑熊重要吗?》一文中提出了道德权重失衡的问题,指出优先拯救黑熊而非帮助贫困儿童的做法引发了人们的质疑。这反映了人们对效益主义道德直觉的怀疑。此外,效益主义模糊了道德选择与非道德选择之间的界限。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爬山来享受乐趣,但也可以不爬山。经典效益主义认为,在这种情境下,爬山便成了道德义务,而普遍观念则认为这与道德无关。这种拒绝将行为简单划分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立场,与苏珊·沃尔夫(Susan Wolf)在《道德圣人》(Moral Saints)一文中的观点相契合。她主张,充实的人生应当包含超越道德约束的选择。然而,这一立场也挑战了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即道德理由应优于非道德理由,从而使这一传统观念变得更加复杂。
针对刘晓飞教授的评议,辛格教授指出,救助黑熊的行为并不存在内在的善好,这一行为是否为善,取决于它对该物种的影响。同时,道德义务的语言通常用于涉及他人利益的情况,而个人享受不应成为道德要求的依据。尽管在效益主义看来,二者都关涉道德,但这种语言可能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田洁教授以教育者张桂梅的事例引入。张桂梅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改变了近两千名贫困女孩的生活,鼓励她们考取大学。自2002年以来,她不懈募集捐款,最终于2008年开校,免除所有学费,确保贫困女孩能够入学。然而,最近发生了一起争议:一位毕业生在接受捐款后选择成为全职家庭主妇,而非追求职业发展;张桂梅对此表示失望,并在该生捐助母校时拒绝接受她的捐款。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帮助者与接受者之间自主权的讨论。张桂梅希望女孩们实现独立与自给自足,但接受者的选择可能与她的愿景不符。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帮助者,如果对接受者的选择不赞同,是否应继续提供支持?这涉及道德责任的问题。因此,如何在尊重个人自主权与承担道德责任之间取得平衡,这是一个复杂的伦理难题。
辛格教授认为张桂梅校长的案例耐人寻味。张桂梅校长拒绝这位前学生捐款的做法,不仅可能伤害了学生的感情,同时并未实现更大的效益。辛格教授继而以有争议的来源(如石油公司)接受资金的复杂性举例,强调如果资金可以用于有益的目的,捐款可能好于给股东分红。此外,辛格教授还提到了条件性捐款的概念(尤其是当朋友可能滥用资金的时候),借此强调了追踪慈善捐赠的重要性。
现场问答
在现场问答环节,辛格教授首先回应了一位线上观众的提问:“为什么个人要去承担由社会结构性问题带来的经济负担?因为只有在过一种可预期可把握的生活、确定满足基本社会福利的前提下,个体才可能有动力进一步贡献他人或回馈社会。”针对这个问题,辛格教授回应,贫困不仅仅是社会结构问题,还可能与地理条件、气候和治理等因素有关。他进一步提出,作为效益主义者和有效利他主义者,需要评估改变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并根据预期价值理论决定最有效的行动方式。
下一个问题来自山东大学的郭鹏教授。郭鹏教授附议了白彤东教授的意见,支持重新考虑“功利主义”的译法。她强调,翻译本身是一种阐释,尤其是在语言差异较大的情况下,翻译可能会引发误解。她还指出,词汇在不同的时代会不断演变,因此我们有责任在当下调整语言以避免误解。白教授随后补充,“功利”一词在中国哲学中有其根源,可联系到宋代儒学“浙东学派”中的“事功”思想。
接下来,有观众向辛格教授提问,关于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平衡情感与理性的问题。辛格教授回应称,情感在效益主义中的确有重要作用,但有时会妨碍理性的道德决策。他引用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的观点,指出人们往往对身边的人产生更强的共情,这可能导致我们给予他们过多的关注,忽视了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因此,我们需要反思和理性控制自己的情感,以确保我们的道德决策更符合效益主义的原则。
针对这个问题,田洁教授分享了她在慈善捐赠时的经验,指出情感在吸引人们参与慈善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情感也是一把双刃剑——过度的情感可能导致“同情疲劳”,反而会迫使人们不再参与慈善活动。因此,在慈善和道德决策中,同时平衡情感和理性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位观众提出了一个关于预期价值理论的问题:高频率发生的微小的快乐(如吃巧克力),能否胜过极低概率发生的重大的痛苦(如不慎导致他人死亡)?对此,辛格教授认为,虽然在理论上,极小的风险可能被忽视,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无法正确权衡这些小概率事件。因此他认为,即使风险极小,我们也不应为了追求小的快乐而冒可能导致他人死亡的风险。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也是为什么效益主义者可能会支持一些“家长式”立法,如要求人们开车时系安全带或骑摩托车时佩戴头盔。
进一步了解效益主义(辛格教授推荐):
J. J. C. Smart & Bernard Williams,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中译本:J. J. C. 斯玛特、伯纳德·威廉斯著,劳东燕、刘涛译:《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Katarzyna de Lazari Radek & Peter Singer, Utilitaria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Utilitarianism.net
文字整理:实习生 马琳、李林壑、陈楚淼
简介
活动主办方:
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
机构
中信书店

活动时间:
2024-10-11
活动地点:
中信书店·启皓大厦店
活动状态:
已结束
直播
嘉宾
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