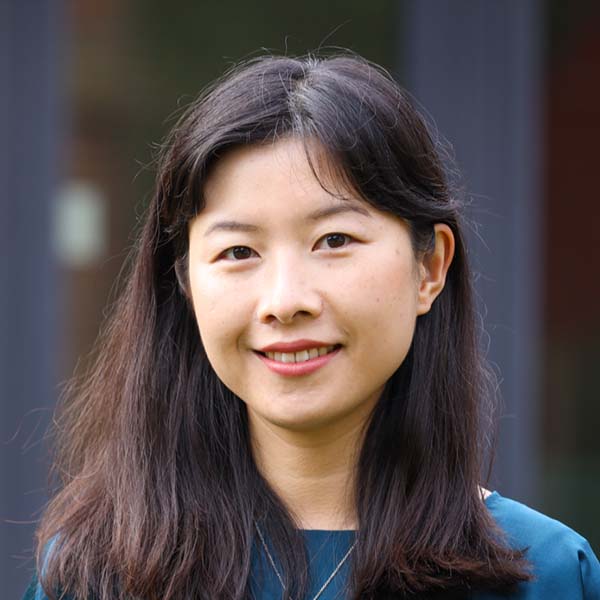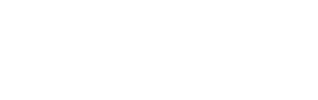博古睿讲座32|羞耻感与幸福生活: 跨越古代希腊与中国的哲学对话
2024年12月13日晚,博古睿讲座系列第32期“羞耻感与幸福生活:跨越古代希腊与中国的哲学对话”在中信书店三里屯店举办。本次讲座由剑桥李约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剑桥大学克莱尔堂(Clare Hall)“李约瑟”研究员、2024—2025博古睿学者赵静一博士主讲,与谈嘉宾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袁艾博士。
近年来,“全球化古典学”运动推动了古代希腊与中国思想的比较研究。本场讲座中,赵静一分享了其2024年5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亚里士多德与荀子论羞耻感、道德教育与美好生活》(Aristotle and Xunzi on Shame,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Good Life)。讲座从跨文化视角出发,结合亚里士多德与荀子的哲学思想,深入探讨了羞耻感在现代社会中的双重角色:“羞耻感”既是一种“负面”情感,又在道德培养和社会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讲座还反思了当代社会对于幸福的理解,特别讨论了过度追求积极情感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
一、缘起:羞耻感的定义与作用
近年来,情感在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领域引发了“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研究者们认识到,情感不仅是个人的内心体验,也深刻影响着人的认知、行为和社会关系。
羞耻感是一种常见却复杂的情感。它不仅深刻影响我们的行为、关系和幸福感,也是文化中重要的道德标尺。尽管羞耻感常被视为负面情感,但它也可能成为自我提升的重要动力。羞耻感是一种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违背社会规范时所产生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既源于外部的社会评价,也源于内心的自我反思。
羞耻感的产生是一种高度自我意识的体现。它不仅揭示了个体对社会评价的敏感性,也反映了自我标准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这种情感既是内在的自我批评,又是外在社会约束的结果,深刻反映了个体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菊与刀》一书中提出了“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与“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的概念。罪感文化的含义涉及依靠“良心”而行善,真正意识到是非对错。耻感文化则更加在意外人评价,依靠外界的约束来行善。相较于罪感文化,耻感文化被认为是更为初级的状态。然而,这种二元划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羞耻感并非天生具备,而是后天习得。一方面,羞耻感是内在化的,它涉及自我评估与反思;另一方面,它又是外向的,因为人的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所塑造的。
二、荀子、亚里士多德论情感与道德教育
近年来,中国与希腊的哲学比较研究成为学术热点。通过跨文化研究,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深入理解各文明的内在逻辑。通过比较,我们得以超越文化偏见,从更广阔的视野思考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基于这种思考,赵静一于2024年在剑桥成立了中国-希腊学术研究会(Sino-Hellenic Network),旨在促进从事古代希腊与中国比较研究的学生、学者之间的联系与交流。
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比较研究即展现了中国与希腊比较研究的意义。他们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但他们都生活在社会动荡和思想混杂的时代。亚里士多德出生于马其顿,在雅典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作为柏拉图的学生,曾担任亚历山大的老师。他的学说主要面向立法者(legislators)。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曾游学于齐国,并在稷下学宫担任过三次祭酒,致力于教化诸侯贵族。
亚里士多德和荀子都高度重视教育。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Politics)中提出:“少年的教育无疑是立法者最应关心的事业。倘若邦国忽视教育,其政治必将衰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The Nicomachean Ethics)中提出:“德性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自然的。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习惯而完善。”
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不同于西方基督教中的“原罪”(original sin),荀子的这一观点认为,人天生具有改变的潜力,能够通过教育和自我修养达到更高的道德标准,因此他有“学不可以已”(〈劝学〉)和“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的表述。他提出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正名〉),以及“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正名〉)。荀子认为,通过礼义教化和心的主宰,人可以约束和引导自己的欲望和情感。
三、羞耻感的哲学分析
古希腊语中体现羞耻感的词组主要有两个:aidōs 和 aischunē,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修辞学》(Rhetoric)中均有提及。Aidōs具有多重含义,不仅指“羞耻感”,还带有敬畏、尊重和谦逊的意味。作为人类身份的一个特征,该术语通常与正义(dikē)紧密相连。它不仅是一种个人情感,还扮演着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的角色。由于年轻人听凭情感(pathē),他们常常犯错误,所以需要aidōs来约束他们,帮助他们少犯错误。而道德成熟的人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事件中,都不应该感到羞耻,因其不会让自己陷入需要感到羞耻的境地。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aischunē是一种由于做了、或正在做、或将要做似乎有伤自己名誉的坏事而引起的苦恼或不安的情绪。羞耻感被视为“半美德”,虽不完全等同于美德,却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
荀子则认为,羞耻感是推动人们修养自身的重要动力,君子时刻反省自己,践行自省。他提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荣辱〉),强调个体应优先考虑道义,而非个人利益。羞耻感帮助个体认识自身不足,并推动自我反省与改进。荀子还作出了“义辱”( 因自身品质感到羞辱)和“势辱”(由外界施加的羞辱)、“义荣”和“势荣”的区分,认为真正的羞耻感应源于个人的道德缺陷,而非外部环境造成的耻辱,荀子强调个人可以通过内化道德标准和良知不断成长。
在方法论上,亚里士多德与荀子都使用了“曲木”这一比喻,来说明教育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不同的人会沉溺于不同的事物……我们必须把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只有远离错误,才能接近适度。正如我们在矫正一根曲木时要过正一样。”荀子的〈劝学〉篇中也有“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的论说。 “矫正曲木”的比喻说明,正如弯曲的木材需要矫枉过正,羞耻感也是一种教育和修养的工具。通过正确的教育与引导,个体可以克服天性中的不足,实现道德上的提升。
四、羞耻感的现代意义
在现代社会,人们倾向于简单地将情感分为“正面”和“负面”,忽视了负面情感的深远意义,而羞耻感被普遍视为一种不受欢迎的情感。人们常常将羞耻感简单地归为负面情感,但如果能够正确引导,羞耻感实际上可以成为一种道德修正的重要机制,促使个体反思并不断改进。赵静一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在《羞耻感能让人变得更好吗?》(Can shame make you a better person?)一文中指出,羞耻感可以帮助塑造更加道德、负责任的生活方式。这表明羞耻感并非仅仅是一种令人不适的情绪,它还可以在我们追求更高的道德标准时发挥积极作用。在“负面情感”当中,恐惧、悲伤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失去、促进成长,成为推动幸福生活的力量;焦虑和悲伤本质上是自我保护的信号,也是人类情感的自然组成部分。幸福不是持续的愉悦,而是一种动态平衡。
近年来,社会过度追求积极情感,市场通过“自我关怀”(self-care)和“抗压力产品”来塑造一种新的幸福概念。然而,这种对积极情感的执着会带来一定的隐患,比如看到他人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完美生活”可能引发焦虑和自卑。正如Delistraty在Aeon中撰文所言:“是什么让‘感觉良好’变成了一项无止境的、竞争性的任务?这种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反而让我们更加痛苦。”这种对积极情感的执着反而可能导致情感的失衡,忽略了负面情感在塑造幸福感深度中的重要作用。
在《黑镜》(Black Mirror)的“Arkangel”一集中,母亲通过脑植入设备监控女儿,屏蔽她的负面情感体验,使女儿无法感知情感冲突,最终导致母女关系破裂。该情节反映了过度干预和控制情感的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成长隐患。所谓“负面情感”实际上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真正的幸福并非逃避负面情绪,而是与之共存,适当地处理负面情感使之产生长远的积极效应。
在数字化时代,羞耻感因“公开羞辱”而被无限放大,其作用和意义也变得更加复杂。羞耻感需要与羞辱(shaming)加以区分:羞耻感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动力,促使人反思自身行为并加以改进;而羞辱则往往具有破坏性,可能摧毁个体的自信心。例如,2021年发生在北京的一则新闻中,一名小学生因课堂表现被教师羞辱的事件,引发了社会对羞辱教育的广泛批评。现代教育理念越来越强调尊重与引导,逐渐摒弃了羞辱式的教育手段。然而,社交媒体的迅速传播却让羞辱成为一种更具破坏性的工具,使个体的隐私和尊严面临更大的威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社交媒体的传播,实施羞辱的老师最终也成为了被羞辱的对象。由此可见,羞耻感本身并非有害,它可以成为道德反省和自我提升的推动力。但当羞耻感被滥用为羞辱,便可能对个体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耻感是一种社会化的情感,连接着个体与社会,是二者之间的重要纽带。真正的幸福并非源于对负面情感的逃避,而在于能够坦然面对并接纳情感的多样性。正如赵静一新著封面——宋代画家马远的《独钓寒江图》所展现的意境——羞耻感是一种促使个体内省的深刻力量,而幸福生活的实现,则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到情感的共鸣。
五、问答环节
有观众针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对情感的描述,提出羞耻感作为社会性的一部分,与罪感形成了两极坐标。羞耻感常与社会评价相关,而罪感更多是内在的反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平衡社会期待与自我价值?
赵静一回答,荀子认为羞耻感不应仅适用于年轻人,而是贯穿人的一生。人很难达到完美的道德标准,但“学不可以已”,学习和修身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如何判断在特定情境中坚持道德标准是否值得? 她举例Netflix电影Joy(《一个奇迹的诞生》)中上世纪剑桥科学家发明试管婴儿技术的历史,科学家们因突破伦理边界而受到社会舆论和教会的批评,但最终却因这一成就获得诺贝尔奖。这一案例引发我们思考:个人在逆风而行时如何判断对错?如何通过内心修行达到道德与幸福的平衡?社会标准随着时代不断变化,而从古代哲学家的视角来看,一位道德高尚的人内心应达到一种境界,即对事物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关于道德情感的讨论中,有观众问荀子是否可以被视为后果主义者(consequentialist)。对此,赵静一回答:荀子认为,先王制定礼义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群体的欲望,而非一味压抑或控制欲望。他提出需要“过滤”欲望,即通过“心”来考虑哪些欲望应当被满足,哪些应被摒弃,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理性引导。荀子既重视社会的稳定和谐,也强调个人的道德升华,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荀子是一位只关心行为结果的后果主义者。
另一位观众的提问涉及古代思想中社会道德与个人修身的关系。提问者关注到,当个人的道德选择与社会规范不一致时,反思应该从修身的角度出发,还是依赖社会的客观标准?
赵静一回应,不管是荀子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都重视行为的动机,强调人不应为获得外界的肯定而作出决定,最重要的是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荀子强调不同性质的“荣”与“辱”,亚里士多德则区分了行为动机——是为了荣誉、至善,还是为了避免恐惧或惩罚——他认为,理想的道德行为应以至善为目标,而非单纯为了外在的荣誉或惧怕惩罚。
关于情感归类的问题,提问者提到羞耻感与其他情感(如害羞、羞涩、愤怒、失望)的复杂性。与谈嘉宾袁艾援引李晨阳教授的观点:“社会的语法”是不断演进的,情感的表达也随人际关系的变化而调整。例如,对“失望”这一情感的分析表明,失望不仅是对现状的认知评价,也可以在提升道德意识中发挥作用。赵静一则指出,羞耻感和其它情感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学习如何理解自身情感并适当地表达情感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如果羞耻感被正确引导,可以成为道德反思的动力;但如果羞耻被放大或扭曲,可能导致情感失控与不适。
针对不同情感的定义是流动而非固定的,羞耻感和其它情感(如“羞涩”等)有一定的交叉。这也是以跨文化视角研究情感史的魅力所在,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化对情感描述的差异。用中文讨论古希腊文本,或是用英文讨论中国古代经典,本身就涉及跨文化的尝试,会生发出一系列有趣的新问题。
文字整理:实习生 李林壑
简介
活动主办方:
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
机构
中信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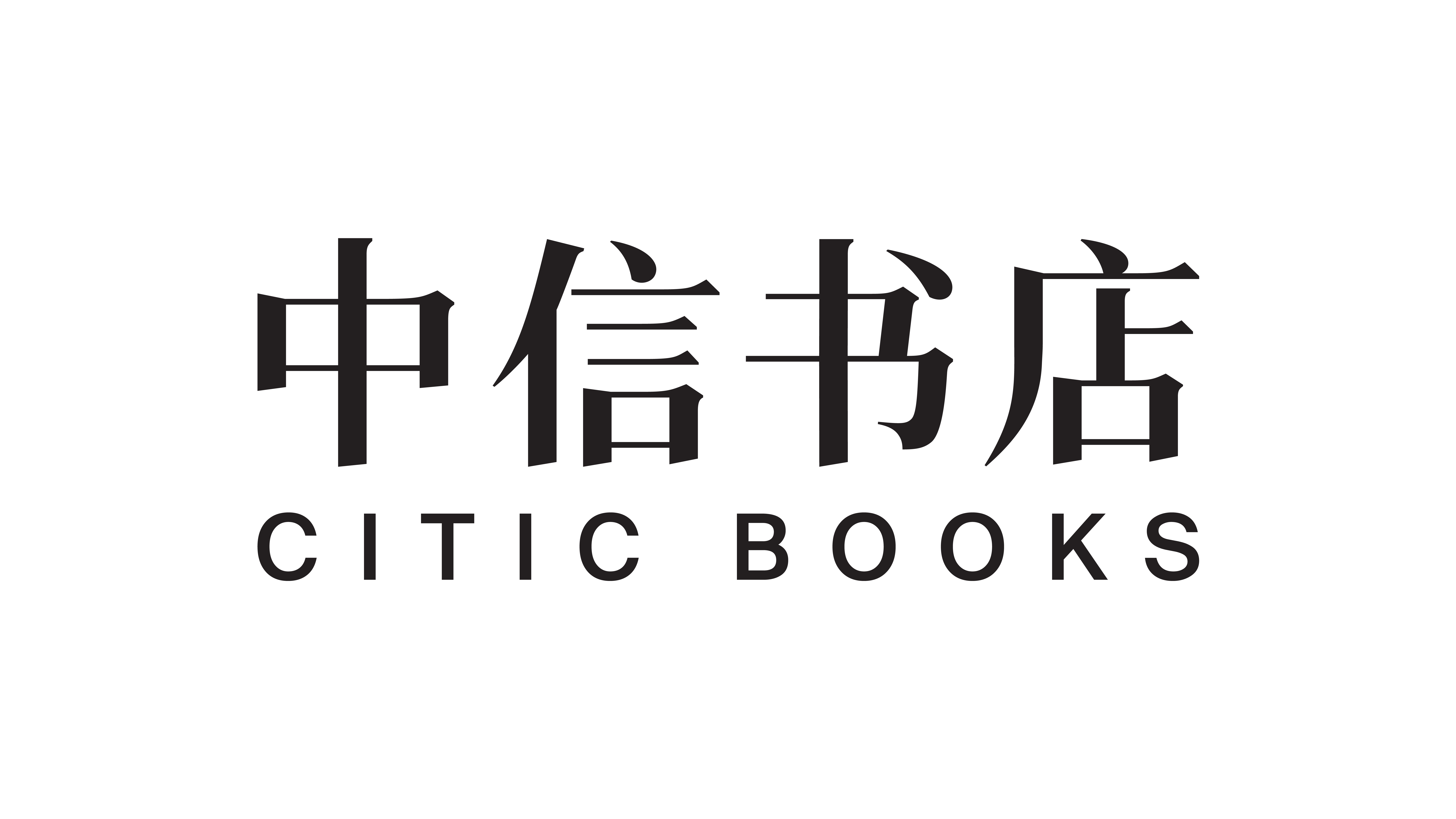
赵静一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活动时间:
2024-12-13
活动地点:
中信书店·三里屯店
活动状态:
已结束
直播
嘉宾
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