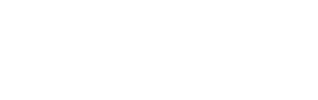博古睿讲座33|流动的身体——从道家哲学到数字生命的身体构想
12月17日晚,博古睿讲座系列第33期“流动的身体:从道家哲学到数字生命的身体构想”在北京中信书店三里屯店举办。本次讲座由云南大学哲学系教授、2024—2025博古睿学者张小星主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2022—2023博古睿学者陈霞和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费多益评议。
讲座回溯了近现代西方哲学中有关身体的诸种争论——从西方哲学根植于基督教世界观的“身心二元论”、道家的“气本一元论”,再到现代西方学界将社会文化框架视为理解和形塑身体重要因素的转向,呈现了多元视角下对于身体和身体观的不同设想。此外,三位老师以赛博格和数字生命的想象为参照,尝试探讨西方哲学和道教的基础世界观会如何看待未来生命形态的身体,进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身体、生命、意识和世界的联系。
从“身心二元论”到“气本一元论”:基督教与道家的身体观比较
张小星首先列举了日常生活中与身体有关的现象,强调了“身体”这一概念是具有双重性的:它是被观看、塑造、使用的客体化的对象,同时也是能动的存在、是行动者的存在方式。客体与主体身体这两种身体形态,可粗略地对应于西方哲学传统中身体与心灵、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在西方哲学中传统中,这一差异曾被解释进身心二元的框架。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便是其经典版本。
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强调物质—身体与心灵—意识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存在——处于空间之中的物质和身体具有几何、物理属性,而作为意识的心灵没有这些物理性质,也无需随身体而消亡。笛卡尔的二元论与基督教“肉身可灭,灵魂不死”的信条相契合。身心二元论也正是在基督教的背景下提出的,反映了基督教世界观得以存续的内在需求。同时,基督教身心二元的框架以上帝为背景。上帝被设置为无限的超验实体,既不同于身体,也不同于心灵。经笛卡尔解读的基督教,也因此预设了身体—心灵—上帝的三元世界观。
张小星指出,基督教三元世界观曾面对至少两个经典哲学困境。首先,作为两种不同的实体,物质的身体和非物质的心灵之间的互动和因果关系,成为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心灵不同于物质,也就很难与物质产生因果作用,而这违背了我们关于身心互动的尝试。其次,作为“超越性实体”的上帝处于时空之外,因而不可认知。近代以来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的尝试多以失败告终;而对上帝直接的神秘感知,其真伪也无法在人类视角下核实。
我们当今所默认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可以看作基督教三元世界观的遗产。通过剔除上帝和非物质的心灵,当代自然主义者在本体论中仅仅保留物质性的存在。从科学视角看,这一观念是科学发展、世界祛魅的成果;但从多元文化视角看,当代自然主义世界观仍是基督教框架“减法”而得的结果。这个意义上,张小星认为,东方的道家哲学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并能部分回答基督教的西方世界观中的一些经典问题。
道教虽然同样承认主客身体视角的差异,却从未对世界进行实体二元化的理论构建。学界普遍认为,道家虽然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本体论学说,却秉持着“气本一元论”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的“气”并非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一种阴阳五行关系中不断变化的能量,既可以展现为物质,也可以展现为精神。道家的终极真理“道”也并非类似上帝的超验实体,而是内化于世间万物、体现在气的运行之中,与气是一元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与二元论相比,道教的这一思想体系更好地解释了身心关系,使身心互动成为可能——身心不再是两类不同的实体,而是在气的互动之中所展现的两种形态。与此同时,气本一元论使终极真理成为可知的存在。道存于气之中,气又运行在时空之内。道士在修行中获得的气感,也就指向了时空之中的气-道状态,从而有可能在人类视角下核实其真伪。
道教将身体视为对应于宇宙万物的能量枢纽。道家对身体的界定,并非“我作为行动主体所能直接控制的事物”,而是“我作为个体生命和天地宇宙的链接”,反映了更宏大的宇宙观。因此,道教不强调解剖学意义上作为物质集合的身体,而是关注身体能量交换的功能。至于身体的边界,由于个体与宇宙对应关系的“符号枢纽”无需固定的边界,道教也就不将身体的边界视为核心问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赛博格和数字生命等概念的出现翻新着我们对身体的认知。作为延伸讨论,张小星设想了东西方哲学框架和身体观会在解释这些现象时的差异。赛博格的可能性提示我们:身体不必由生物组成,而是同样可以包含假肢、外骨骼、脑机接口等。这些“人机共生”的想象,打破了身体的传统生物边界,也使主观视角的身体外延不再受空间局限。
张小星认为,赛博格不仅提示了身体可能没有明确边界,也意味着身体无需满足空间的切近性。在“阿凡达式”的情形中,大脑可以隔空操纵远处的身体。同时,赛博格也挑战着我们对主体之间身体关系的预设:若多人共用一套外骨骼,他们的身体是否还有明确的区分?将意识上载至虚拟现实的数字生命这一设想,也对身体观提出了的新挑战:数字生命是否还有身体?如果有,数字生命的身体又是什么?是虚拟现实中的身体,还是承载虚拟程序的硬件?
张小星认为,道家不会否认赛博格与数字生命的可能性,但会因为两者不符合子午流注等身体能量的运行规律,而拒绝将其视为完整意义上的身体。所以,尽管道教和当前自然主义世界观对生物性身体的外延判断基本等同,双方对赛博格和数字生命的身体判断却会存在差异。当然,在谈论道教身体观时,或许应区分两点:一是道教如何描述现实的身体,二是道教对身体有哪些本质性定义?或许,子午流注等规律只是道教对现实身体的描述,不必构成其身体观中的本质因素。区分这两点,有助于以更开放的视野理解道教对未来身体形态的可能判断。
可延展的开放身体:道教身体观的多维解读
陈霞从多个层次详细论述了道教的身体观。她指出,在道教的思想体系中,“身”、“身体”和“生命”占据着重要地位。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都曾强调,身体之于身外之物(不论是钱财、名利或者天下)具有绝对的优先性:身体是原生的、第一性的、自然的、先在的;一切都可以从自我的身体开始。“我命在我不在天”、“仙道贵生”等口号和各种养生也反映出道教对身体的重视。
身体的在先性不仅表现在对生命的强调上,还体现在道家打破身体边界而对身体进行的种种延伸和外推当中,体现在身体与世界的交道之中。陈霞认同张小星谈及的道家对身体边界的认知,并用庄周梦蝶的故事进一步论证:道家总是试图打破、模糊身体与外在世界的边界。道教把国家看成身体,赋予了身体以政治性:既然一个国家可以被视为一个人的身体,治身与治国原则相通,那么治国就应遵循天性、顺应人性,无为而治;道教把天地、宇宙、自然也视为一个巨大的“宇宙身体”;人体是一个与自然运转一致的、包含天地运行信息的内宇宙。
道教还把身体延伸至超验界。与基督教不同,道教认为,宇宙中有多种神灵居住,身体内也有相应的神灵居住。由于身体里住着这么多神灵,人体也成为一座“万神殿”,而不是一些西方哲学家所认为的“身体是约束灵魂的监狱”。
此外,身体在道教话语中还具有美感——华盖(眉)、玉枕(脑后)、灵根(舌头)、玉都(身)、重楼(咽喉)——这些对身体和身体部位的比喻,以及道教对人体山水画式的描绘,都彰显了身体的价值和地位。
陈霞还尝试从道教的角度回答了西方哲学中的身心关系问题。“神形俱妙”、“形神相需”的理念所显示的是道教肉身精神化、精神肉身化的追求。身心在“身得道,神亦得道;身得仙,神亦得仙”的动态的过程中不断相互融合。正因如此,她认为,在数字生命时代,道教努力守护身体对他人和世界的独特感知、经由身体而与世界打交道、获得切身经验、延长自然生命的长度和提升生命质量的追求,更显得独特而珍贵。
身体:从自然化到符号化
费多益首先高度评价了张小星讲座的内容。她说,中西方文化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不容易入手或切入,而张小星把身体作为文化碰撞的桥梁和纽带,是个巧妙的路径;把好几个领域的关键点行云流水地串起来,并提炼和延伸到一个新高度。比如,从道家的身体没有明确的边界,联想到极端的情形,推出两难的困境。又比如,在道家身体厚理论中,哪些是描述性的、哪些则具有理论规范性,这一问题值得所有文化的身体理论去思索。总之,张小星关于中西方两种“身体”之间的对话,通过细密的论证,开拓出富有生长性的意义空间。
其后,她补充一个关于身体研究视角的不同看法。她说,身体观的探索曾经面临心身二元论与自然主义解释之间的抉择,正如大家每每提及的笛卡儿把身体和心灵看作两个本质不同的存在物。不过,从19世纪开始,哲学家不仅以新的态度看待理性、情感、思想、意志,而且重新考察人的身体及其与精神的相互关系。尽管他们的理论有差别,但共同点都是从身体的物质性出发,使身体抵达某种社会实践的层面,让身体作为世界的出发点。到了20世纪,哲学家对身体的解读,则力图弱化其中的自然化成分,并且融合了不同视阈的价值判断,触及到了人类社会和文化以及主体最深层的本质问题,把身体从“心身”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或从注重身体体验的角度,或从注重身体的社会意义与象征意义的角度,挖掘对“身体”的理解。
正因如此,身体已经不是本己的身体,而是被纳入物质世界中的、活生生的身体(lived body);既包含作为经验结构的能动的身体,也包含作为认知机制的情境或环境中的身体。同时,人类身体各个部位的功能和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和限定,它的活动方式和行动效果也直接在社会文化中呈现出来。比如,一名男子拥有健壮的肌肉,这表明他发育完好、体魄强健,也体现了他的雄性气质和力量。但在近代和中世纪的主流文化中,人们容易把肌肉跟丰富的职业化比赛、体力劳动者甚至是带镣铐的囚犯联系起来。不过今天,肌肉完美、结实成熟的身体不再意味着底层等级的身份,而是意味着一个人爱惜自己,拥有充沛的活力,还彰显了一种自律和意志力。
总的来说,现代身体理论已经摈弃了身心二元对立的思路。然而有意思的是,围绕身体展开的研究仍然存在另一些对立。比如,在本体论方面,面临着基础主义还是反基础主义的选择;在认识论方面,发生了建构主义者和反建构主义的争论。因此,费多益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打破认识论与存在论、身体本体与表征/话语之间的二元分立,强调身体本身的多元性,即“身体”是物质的、体验性的、欲望的、可变的、活生生的,同时又是思想的、情感的、社会的。这要求我们既关注身体的内在结构、组织、约束和保护,又关注根据社会组织和社会稳定性对身体的欲望、激情和需求进行控制。通过这种综合性的视角,让身体成为一种能够体现人与人各自根本性差异的存在。
最后费多益向张小星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数字生命可以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那么考试作弊与通过数字生命获得试题答案,这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吗?
观众互动环节:数字生命的跨文化哲学对话
在互动环节,张小星同样从庄周梦蝶的故事出发,回应了陈霞关于“道家在数字生命时代依然珍爱自然身体”的观点。他认为,尽管数字生命的人造特质使其缺乏道家身体的神圣性,但由于道家将“身体由什么物质构成”置于次要的位置,而更注重身体与外界的互动和感知,因此数字生命只要拥有能与外界保持联系的“身体”——无论作为硬盘还是虚拟程序——就能够在道家的世界观中存在。
针对费多益的提问,张小星提出,数字生命在考试时查阅资料是否算作弊,要看其虚拟现实中社会规范的设定。在现实世界中,“不能查资料”本身就是考试的要求。对开卷考试而言,查阅便不算作弊。所以,数字生命的某些行动是否违规,取决于其虚拟世界中的规则。由于虚拟世界的设定有着更高的自由度,数字生命有可能遵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规则。
陈霞进一步讨论了张小星对“道家视角下的数字生命”的主张。她再次回到庄周梦蝶的故事,借由“数字生命是否也会做梦”的问题重申了数字生命的身体与以肉身为基础的人类身体之间的差异。她强调,庄周梦蝶的寓言暗示了道教将万物视为可与人“嬉戏”的万物平等观,同情心和同理心可能是人与人工智能、数字生命的最大差异。她肯定了费多益提出的“允许身体的多样展开、鼓励身体的多元存在”的主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包容的社会氛围,允许身体潜能的唤醒和充分发挥。
费多益回应了数字生命的问题。在她看来,身体观和生命观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对于“赛博格和数字生命是否可以构成身体”这一问题的解答,要诉诸我们的生命观,即:生命是什么?
针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实在论者强调,用人工方式创造的数字生命完全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生命,生命是一种行为而非一种物质材料。反实在论者则认为,数字生命只具有形式特征,不具有自然生命的其他物质质料特征,因而不是真正的生命。
可以看出两派主要是基于数字生命和自然生命在特征上的异同来判定两者是否具有相同的实在论地位,其分歧在于如何理解生命的特征。对此费多益认为有两点需要强调:1)数字生命是一种借助数字技术来显现的实在,是依赖数字技术功能性存在的产物;2)数字生命是人们创造的一种符号实在,它是对生命本质和特征的新表征手段,即以数字技术形态呈现的表征意义的符号形式;因此它属于人心理建构的产物。
与生命观密切相关的是如何界定意识。为此,费多益表示,讲座中涉及的观点,比如“意识虽然需要物质基础,但不需要依附于特定的物质形态。碳基生命可以有意识,硅基生命也可以有意识;数字生命的物质基础足够复杂,就能够重现每个人的意识”,这些在心灵哲学中已经受到诸多批判。而如何界定意识本身就是一个棘手的课题。
当被问及讲座主题“流动的身体”该如何理解,张小星认为,这个概念有至少两个维度,即身体边界的流动性,以及身体概念和定义上的流动性。陈霞在回答“道家视角中‘谁来控制身体’”的问题时强调,道家的“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而是“道”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姿态,让万物“自然而然”、“自己如此”地对“物”的不主宰。作为核心力量的道只会产生并创造万物,但不会掌控万物的进程。“我命在我不在天”正暗示了这种将控制权下放至万物手中、让“每一个万物成为它自己”的开放性。
文字整理:实习生 马琳
简介
活动主办方:
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
机构
中信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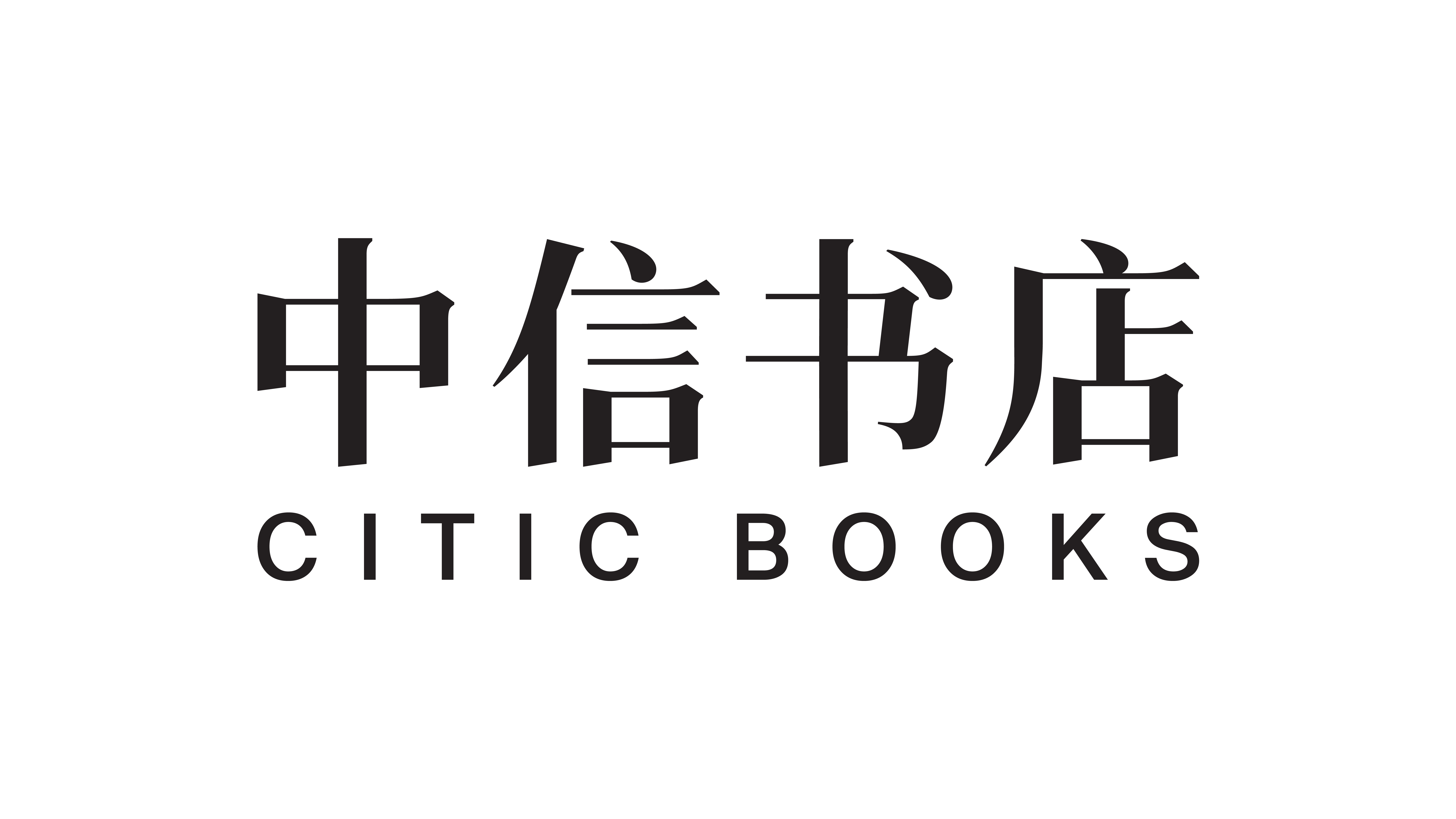
活动时间:
2024-12-17
活动地点:
中信书店·三里屯店
活动状态:
已结束
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