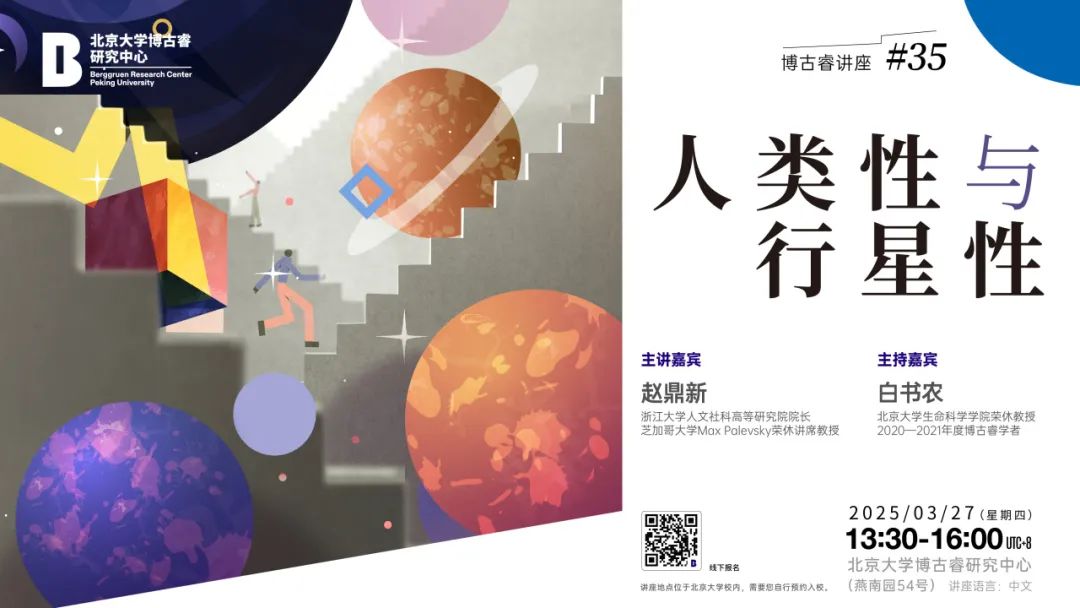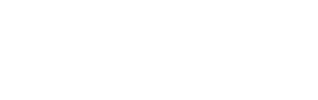博古睿讲座34|动词思维与新启蒙
2025年3月26日下午,博古睿讲座系列第34期“动词哲学与新启蒙”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4号院举办。本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2018—2019博古睿学者赵汀阳教授主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2024—2025博古睿学者孙向晨担任主持。
赵汀阳教授指出,在人工智能与技术浪潮的冲击下,传统启蒙的“名词思维”已经难以应对现代世界的复杂与多变。名词思维以分类和定义为核心,强调事物的静态属性,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所贡献,但这种思维方式无法有效解释大量涌现的动态、不确定的现象。或许我们迫切需要一场新启蒙:在名词思维之外建立动词思维,以理解名词思维难以解释的动态存在、不可测的涌现与文明的创造性奇点。
名词思维的形成:人类认知的路径依赖
早在1998年,赵汀阳教授就在《一个或所有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动词思维”的概念。近年来,他在重新深化这一主题的过程中发现:由于人工智能继承了“名词思维”,诸多复杂问题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虽然“复杂科学”致力于对还原论和概率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展开深入研究,然而三十年来,其方法论的推进依然受制于名词思维,因而难以应对复杂知识带来的挑战。这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们的语言结构是否限制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赵汀阳教授观察发现,人类的语言几乎无一例外皆以名词为本,其他词性则围绕名词展开,只发挥辅助性的语法功能。这种以名词为焦点的意向性特征,引导我们的思想主要聚焦于两大问题:
其一是“什么是什么?”。这是所有知识的基本主题,涉及概念、定义乃至意义的构建。因为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为我们对概念所作的有效的定义及分类。
其二是“以什么去解释什么?什么导致了什么?”。这触及了因果关系的探讨,也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因果关系的探索通常是通过名词系统中各个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对比来实现的。
这两大核心问题,构成了名词思维的框架。名词构成了我们生活、思想和知识的共同话题(topics),围绕这些话题,我们编织出思想的“故事”。从亚里士多德式“种加属差”的分类学,到现代数理逻辑中的范畴论和因果科学,乃至人文社科的规章与身份制度,均是基于名词秩序构建的知识结构。严格来说,除了专名,所有名词都是形而上学。知识的全体相当于一部关于名词的百科全书,先验的秩序支撑着我们的语言和思维活动。
如果我们还原语言的初始状态,以名词为核心的认知路径是如何形成的呢?赵汀阳教授认为,从简单的信号系统到复杂的精神世界,语言发展经历了一次“创世纪”。构成这一历史奇点(singularity)的便是“否定词”(negation)的发明,它带来一系列重要的认知推进。
首先,否定词引入了可能性的概念。在否定词出现之前,语言只表达事实性(actuality),而否定词的出现使得存在论上出现了无穷多的可能世界。其次,否定词赋予了语言自解释的能力,语言不再仅仅是对事物的直接描述,而是能够对其自身做出解释;同时否定词也推动了意识的自我反思能力。再次,否定词也标志着未来的诞生。在自然界中,时间只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否定词提前想象并表达一个尚未存在、但提前到达的事件。有了未来,时间才有了意义。最后,否定词在逻辑上引入了真假的概念。命题“p等于p”没有实际的意义,但通过引入“not”,我们便能够区分出命题的真假,这也迫使我们对事情进行明确的解释与赋值。
因此,否定词不仅是语法上的革新,也是一场思想的大爆炸,让人类从单纯地描述世界转向更深刻的思考。
此外,从经济学和现象学两个角度来看,名词成为语言起源阶段最常用的词语类型亦有其原因。一方面,在原始社会,生存是首要任务。信息传递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部落的存续与繁衍。名词因其高度概括的分类属性(一个名词可以代表一类事物),具备信息经济学上的优势,成为信息传递的最佳载体,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另一方面,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思考需要明确的焦点,因此我们必须将复杂的现实世界简化为可把握的对象。静态的名词能够帮助人类清晰地识别、聚焦特定的事物,人类因而能有效处理环境中的信息。
复杂世界的内在要求:从静态到动态的认知转型
名词为本的语言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知识组织能力,但它最显著的局限就在于无力解释存在的动态性、复杂性、涌现性。名词逻辑之所以不足以理解动态的事物,原因之一在于:它凭借分类学的思想秩序,虚构出了一种等级制的存在秩序。分类学作为名词思维的基础应用,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坐标系。人类通过为事物分配特定的值域,实现对事物的迅速识别与精准定位。
关键问题是:我们所做的分类真的是基于事物固有的属性吗?是否存在一种纯然客观、与人类意图无关的分类方法?一旦回顾不同文化中的分类体系,就能发现名词分类的相对性。中国传统分类法注重以人为本,即根据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分类,如益鸟与害虫的划分。这种分类法在生物学上可能并不严谨,但却对人类生活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此外,中华文化的分类学常将事物的外观特征作为分类依据,象形文字乃是一例。这种“以貌取物”的倾向比西方基于本质属性的分类更符合人的直观经验。因此,分类学是否真正言说出存在,事物是否如其所是那样被分配,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名词思维的另一大局限在于:它还试图形成关于事物的封闭性定义。在分类学的基础上,名词思维进一步推动了概念系统和形式逻辑的发展。概念需要为每一类事物建立明确的边界,以区分内部与外部。这种封闭的概念边界为认知提供了清晰的框架,也促进了西方围绕“to be”展开的形而上学。
“是”(is)在哲学中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表示“归类”,例如“A属于B”或“A大于B”,表达事物之间的分类及层级关系;二是表示两者之间的等价关系(equal)。分析哲学通过这两种方式对语言进行逻辑还原,使语言更加清晰易懂。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将语言分析为一个函数关系式,即通过“x=f(y)”来理解事物间的关系。然而,此类等价只能在封闭且静态的系统中实现。严格来说,只有数学才能做到真正的定义,因为数学恰恰是用定义创造了概念,通过先验的公理约束实现自我指涉的闭环。然而现实世界则是动态的、开放的,甚至充满了漏洞,为概念划定清晰边界只是名词思维的理想化投射。
再者,如果“是”要表达“存在”的关系,那必然涉及“存在等于存在”这一命题。这种完全重合的关系要求主语必须包含一切事物,成为一个包含所有集合的全集,包括自身。然而这会导致“全集悖论”(即罗素悖论——自指的全集系统必然导致矛盾)。然而西方哲学认为,在全知全能的上帝存在的前提下,这种逻辑关系是可以成立的。上帝作为全集,被定义为存在本身,而非对象化的存在者。“God is”这一说法规避了自指悖论,同时维系了存在论的根基。这种解决方案也揭示出形式逻辑的底层思维:它以名词作为基本单位,架构了一个集合论世界。这是我们理解世界最根本的认知工具,帮助我们取得了无与伦比的知识成就。
然而随着科学的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和量子力学等新兴领域的崛起,传统的名词思维逐渐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思想需要增加新的形而上学维度,揭示隐藏在传统哲学光谱之外的事情。
当我们把思想的焦点从名词转向动词,我们将获得另一种关于存在状态的描述。传统的名词体系在静态范畴的构建中展现出了卓越效能,能精准表达确定性、稳定性、必然性、封闭性、独立性等意义,却难以捕捉因果性、变异性、不确定性、可能性、偶然性、开放性、连续性等动态意义。名词思维的局限性促使我们寻找更适应动态交互和复杂系统的表达系统,而动词思维的引入或将弥补这一不足。
动词作为元语言:数学、逻辑学与语言学的合作空间
赵汀阳教授认为,人类动词思维相对薄弱的原因,可以追溯到约五六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那时,人类朴素的生活最需要传递的信息是物体的识别和分类,这一需求促使名词优先发展成为语言的核心元素。在这个过程中,动词主要发挥提示的功能,无需表达复杂的动态关系。
尽管名词思维在人类认知发展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通过与数学家、逻辑学家合作,我们或许能搭建一种以动词为基础的思维体系,即动词思维。数学通过函数表达动态变化,已具有部分的动词思维。其中的动词(“+”和“-”)被定义得非常精确,但仅适用于可量化的部分,所涉及的语义领域远远小于动词的语义领域,目前能处理的动态关系十分有限。
在逻辑演算中,名词思维和静态推理依然占主导地位,“蕴含”(imply)是唯一表达动态关系的词汇。它的确能有效处理真值的传递性(“A蕴含B”),但却无法很好地表达动态、经验世界中的因果关系。比如,“A蕴含B”并不等同于“A是B的原因”,因为蕴含描述的是从一个命题到另一个命题的推理,而因果关系涉及更复杂的动态交互,后者是现有逻辑框架难以涵盖的。
莱布尼茨曾开创性地提到形式逻辑的局限性,并试图通过“充足理由律”(即任何判断都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来弥补其不足。然而,充足理由律过分依赖存在论,无法在严格的逻辑框架中表达。若要对某一现象给出完全充分的因果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整个世界”是这一现象的成因,毕竟没有任何理由足以排除某个因素作为变量的可能性。因此,这种无法完整表达的“充分理由”在科学体系中就显得不成立,尽管对于上帝来说,它又是成立的。虽然这条规律不太适用于经验世界,但它启发我们思索当前名词逻辑的不足。动词包含的某种存在论能力,也许能引导我们走向一种尚未被充分开发的思维结构。
赵汀阳教授建议,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哥德尔式的自指反思,来反思语言和知识系统自身。哥德尔揭示了数学体系中存在一些“真”却无法在体系内部证明的命题,由此迫使整个数学系统面对自身边界。这种结构性反思为动词逻辑的设想提供了可资借用的范式。鉴于人文知识体系的开放边界和松散结构,内部的反思需要通过构建跨知识系统间的相互反思来实现,即运用他者的外部视角替代镜像式的自指反思。具体来说,就是以动词作为反思名词思维的元语言(metalanguage)。这种思路不要求给出封闭系统内部的自洽解答,而是通过引入动词的维度来揭示原系统的局限。
传统知识体系的元语言困境在于自我指涉的循环。所有语言最终都需要通过自然语言来解释,包括数学语言。自然语言在承担元语言功能时,自身也是被解释的对象。在这个循环中,传统语言系统的核心是名词,所以解释也是围绕名词展开。因此,当我们试图用自然语言反思自然语言时,实际上仍然是以名词系统去解释名词系统。这种做法使我们陷入静态定义的无限递归,缺乏跳出自身的力量。兴许动词元语言(用动词解释名词)可以充当异质性的认知杠杆。
赵汀阳教授的设想是:构建出一个动词系统,将每个名词映射到一组与之相关的动词解释中,从而使原本静态、被定义的实体(what)获得一组过程性、动态的诠释(how)——我们不再拘泥于事物“是什么”,而是关注它“如何成其为它”。尽管这种转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哥德尔式自指悖论,但在功能上具有相似的反思效力。
哥德尔悖论要求系统面对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动词元语言通过引入动态维度补足了当前静态维度所遮蔽的内容。这种跨维度的解释方式正是对系统边界的揭示与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名词系统宛如一张分布图,标定了事物的位置;动词系统则像一张营造图,描绘了这些事物如何形成、彼此如何关联、如何持续生成。因此,如果说传统的形而上学试图“以空间理解时间”,那么动词哲学就是尝试“以时间理解空间”。
这种语言的转向,不仅意味着思维方式的改变,也预示着一场新的认知范式革命。在启蒙时代,以理性和名词逻辑为基础构建起“理性人”的知识体系。今天,这一体系的能量行将耗尽之时,我们或许正步入一个新启蒙的时代。
在这个新时代,动词思维可能成为思维转型的核心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并未为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提供全新的思维模型和逻辑结构。讲座最后,赵汀阳教授不无幽默地指出,也许当我们真正掌握了动词思维的奥秘,并将其反馈给人工智能时,我们也许就能在未来的技术化生存中,找到一种“被幸福地统治”的方式。
文字整理:何奇睿(实习生)
简介
活动主办方:
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
机构
赵汀阳
学者活动时间:
2025-03-26
活动地点:
北京大学燕南园54号
活动状态:
已结束
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