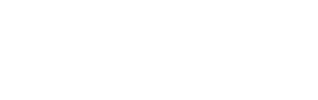当“俳句”遇到“双螺旋”
内森·加尔斯

一种令人感到焦虑的认识正在形成:最新的科学与技术发展非常重要,但是,它们不能仅仅被掌握在科学家的手中。哲学家、艺术家、还有很多其他尚未开始这样思考的人们都需要参与到其中,探究其对人类变革的影响和意义。这是上周在洛杉矶弗里泽举行的一个关于科学与艺术会议讨论的主题。
“我们正在迈入一个可以构造自己DNA的时代。同时,也将创造诸多原本不存在于自然界中的‘自然存在’”,人类学家 托比·芮思(Tobias Rees) 提出,“当我们进入后人类时代,自然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作为博古睿研究院人类变革项目负责人,他进一步表示:“我们必须解决好19世纪的概念。但是,也许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开启当下未知的未来。所以,需要哲学家和艺术家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
艺术家阿格涅斯卡·库兰特(Agnieszka Kurant)回应这一点:“我们目前已有的理念尚不足以应对所面临的混乱状况。因此,必须创建新的模型、词语库和工具手段,以便用新的逻辑来进行思考,从而重新构建我们的世界观。”
德鲁·恩迪(Drew Endy)赞同上述说法,并提出,“这些思考对未来人类的意义在哪里?”对于这位合成生物学家来说,这些进展提供了“考虑一种新的文化操作系统的机会——科学、工程同哲学、艺术的结合”。
事实上,在科学技术的飞跃正在重新唤起文学、艺术学、哲学乃至宗教等领域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可定义人类在宇宙中位置的新起源以及命运的基础问题。
正如亨利·基辛格敏锐地假设的那样,“启蒙运动始于一种新技术传播的哲学见解。而我们的时代正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它产生了一种潜在的主导技术,以寻求指导哲学。”
包括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内的许多当代哲学家,一直在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操作体系——它们会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出现。根据斯劳特戴克的说法,互联网和基因时代的信息,将会把人类及其用于改造自然的工具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崭新的操作系统。这种“后形而上学”的状态,不仅消除了“主观人”与“客观精神”之间的分离,而且也消除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差异。
斯劳特戴克发表在2014年《新视角季刊》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灵魂与事物、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自由与技术的本质区别,无法与那些通过其自身的结构将精神与物质“成分”相混合的实体相适应。
“控制论”作为智能机器的理论与实践,现代生物学作为系统环境单元的研究,迫使旧的形而上学划分问题被重新提出。 在这里,客观精神概念转化为信息原则。信息作为第三价值进入思想和事物之间、反射极和事物极之间、以及精神和物质之间。智能机器,就像所有文化创造的技巧一样,最终也迫使人们意识到“精神”。反思或思想融入到物质中,并且随时可以用于进一步培养。因此,机械和技巧是记忆或反思转化而成的目标。
有德国哲学家认为,“在这样一个再概念化的过程中,‘我’和‘世界’的星辰失去了很多光彩,更不用说个人和社会的极度对立了。但最重要的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形而上学区别逐渐消失。究其原因,是因为区别的两个方面仅仅只是信息状态及其处理过程。”
对于斯劳特戴克来说,这种信息生态学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与他人、他们的世界和他们的工具之间新的融合身份。人类不再是一种分离的身份,并将这种联合智能系统称为“人类技术”。
一些诗人试图思考一种新的文化,当人类和技术结合在一起时,这种文化可以将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记得在几年前的一次谈话中,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表达了他对“硬”科学与被定义为“人文学科”的科学相分离的担忧。“也许我们都会意识到我们坐错了火车”,诺贝尔奖得主沉思着说,“歌德有一种直觉,那就是有些事情出了问题,科学不应该与诗歌分离,应该保持对人类的尊重。作家布莱克(Blake)也这样认为,也许我们会回到一个非常丰富的时代,在这里,诗歌将再次与科学并驾齐驱。”
由此产生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新的星辰中,人类居住在哪里?人类受到尊重的基础是什么,它又将如何被尊重?
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当“俳句”遇到“双螺旋”时,我们将会找到一种新的语言来谈论我们已经进入的未来世界。